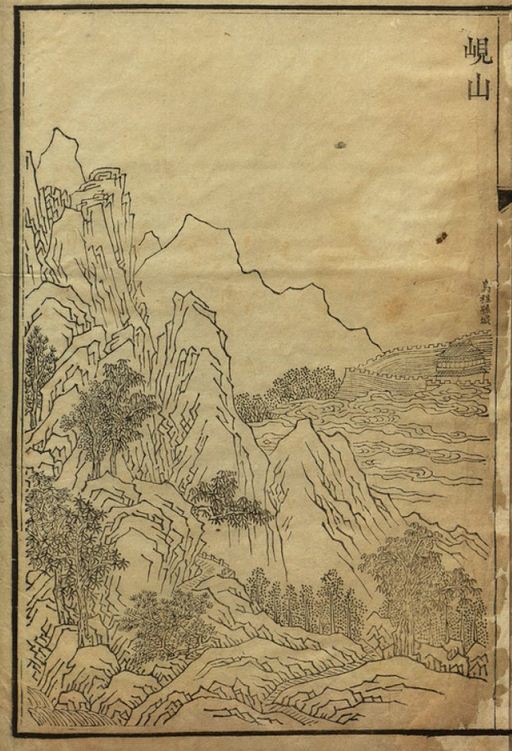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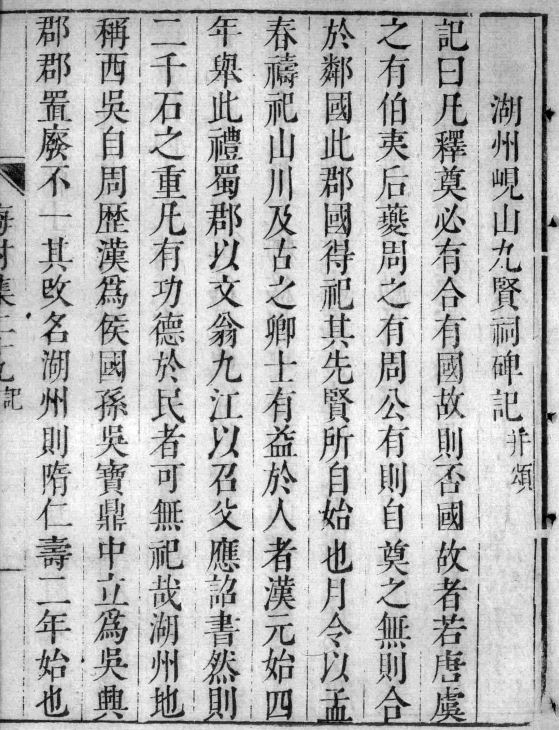
吴绮在湖州任官时,将岘山(上图,选自《名山图》)上的三贤祠增扩为九贤祠,祠中供奉王羲之、颜真卿、苏轼等在湖州任官的名贤,同时代著名文学家吴伟业曾写《湖州岘山九贤祠碑记》(下图,选自《梅村集》)以记其事。
雁过留声,人过留名。名声的背后,寄托的是对其人的怀想,饱含的是对未来的希望。时光流转,因民生而立、依民声而传的名声,却如同束束亮光,时或尘封而难以遮挡,在历史的长河中,不时散发光芒。譬如,有着“三风太守”之称的吴绮。
吴绮,字园次(一称薗次),清代扬州府江都(今江苏扬州)人,康熙五年(1666年)至康熙八年(1669年)任湖州太守,“德政惠民,多风力,尚风节,饶风雅”,百姓称之为“三风太守”。
多风力——勇作为敢担当
康熙五年春天,在友人的送别中,他来到浙江湖州任职。此地原本山清水秀,物阜民丰,但当时舞文告密之风尤甚,恶人王式、王春等罗织交关,同党达千百人,控制官府,祸害乡里,政务松弛,民不聊生,“男女鬻于昏途”,“魍魉行于白昼”,以致上级查勘也担心被举报而不敢用力。
吴绮到任后,微服私访,走遍湖州贫困地区,了解乡里村墟情况,期间有时遭到醉尉呵斥、邮亭侮辱,他也不动声色,不露痕迹。掌握情况后,他周密布置,一举抓获魁首及主要党羽钱玉涵、唐文等十多人,予以严惩,史料记载其“单舸擒治”,颇类辛弃疾单骑追贼。当时总督深有感触地说:“使吴君早至,吾何至为王式所持哉?”首战告捷,吴绮并未停手,对行凶乡里的菱湖沈柬之、西湖严君球等实施抓捕,前者予以杖杀,后者畏罪自杀。三次除恶,引起当地极大轰动,史书记载,“湖人欢声动天地”,可谓深得民心。
在湖州三年多,他敢说敢做,从不畏首畏尾。惩恶同时,他还着手严治鱼肉乡里的兵丁、奸吏。抓到欺霸乡里的驻军营卒,他不是重拿轻放,做做样子,押回军营责令改正,而是不打招呼,不做人情,依律对带头人直接严惩。驻军大帅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看到吴绮动真碰硬,他不再放任自流,而是严令部下,“吴守非易与者,汝曹勿入其境也”。
湖州盛产蚕丝,其选料挑剔,精工细作,光泽度、韧度均远非寻常蚕丝所比,颇受海外欢迎,当时朝廷实行海禁,湖州一些地方官吏以海禁登记为由,索拿卡要,捞取好处。吴绮得知后,做了一个大胆决定,当庭焚烧籍簿,杜绝此弊。他说,“苟有失误,太守自当之。不以累吾民也。”
其实,吴绮勇于担当的个性在担任京官时就有体现。当时京城街道路面养护由工部牵头,五城司坊官负责,遇到的多是掘坑挖坎、盖房占道、傍城使车、撒放牲畜等城市管理的老大难,其中关系复杂,面广水深。相应的管理体制几经变革,难以奏效,康熙登位后将街道分左右翼,令工部满、汉司官各二人管理。康熙二年(1663年),吴绮担任工部正郎,分管街道左翼,上任后他严抓严管,快刀斩乱麻,“挫抑豪强,一时肃然”,取得较好的震慑和治理效果。在任两年多后,他被派往湖州。
尚风节——秉风骨持节操
在下属看来,很多时候吴绮并不像太守,倒与赶考的书生没什么两样,在府衙,除了办公,就是翻翻读读,写写唱唱,家中也不像官宦之家,屋内除了绳床棐几和散发着青光的灯火,别无长物。
吴绮当太守三年多,去官时,清贫如洗,连一件像样的衣裳也买不起,甚至回扬州老家的盘缠也不够,后来在女婿和友人的帮助下才回扬州买房置地,安度晚年。吴绮觉得对不起家人,其妻黄氏倒是坦然,安慰说:“以清白贻子孙,何必捆载以归,而敛百姓之怨乎?”
古代太守号称两千石,在清代其俸禄加上养廉银总收入并不少,但吴绮政事之余,热衷公益不惜钱财,过湖州苕川仪凤桥时发现修桥缺钱,直接解下金带襄助,兼之常常接济他人,家中难免入不敷出。为此,他典当过友人赠送的裘衣,质卖过夫人的耳环,但从未以权谋私。
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,作为一方主政,无需刻意敛财,自然有人奉送,王式党羽唐文被抓时,就行贿三千金希望免其罪行,吴绮却理也不理,“挥去弗顾也。”反过来讲,吴绮敢于执法从严,也正因为他自己形端表正,没有私心。他主持湖州“试士”(古代为授予官职而考试士子),公正公开,“暮受卷而朝榜发”,不留任何想象余地,不余任何操作空间,送礼的说情的打招呼的一概不见,才能出众而出身寒微的考进必取。其选拔的寒门子弟中,后来考中进士的不在少数,甚至有榜眼、探花,士人为此专门立碑以表纪念。
担任湖州太守三年多,吴绮因为忤上官遭弹劾。推究其惩豪强、兴民生的作为,居官简静、为人坦率的性格,以及登临唱和、作诗填词的喜好,自然为当时官场和地方劣绅难容。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百姓的态度,五十岁生日时,自发来为他祝寿的父老子弟多达万人,被劾离职时,国库尚有缺项,很多百姓自发带着铜钱,哪怕只是三枚五枚,投到府衙前的箱子里,希望尽一份心力,“无以累我公也”,其受百姓爱戴如此。
饶风雅——复胜迹兴文化
湖州自古风雅。唐代颜真卿担任过五年的湖州刺史,主持编纂《韵海镜源》,留下了《湖州帖》《刘中使帖》等烛照千古的书法名作;宋代苏轼挥毫写下《墨妙亭记》和《孙莘老求墨妙亭诗》多篇诗文,在湖州太守任上发生的“乌台诗案”更为后人留下无限伤感;元代赵孟頫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湖州度过,留下了《吴兴赋》《湖州妙严寺记》等若干墨宝。仅此三贤,即令湖州生辉,文人慕往。
来到这个“文化之邦”,吴绮看到的却是古迹凋敝,名胜不彰。有感于斯文零落,他重建了宋代湖州太守孙觉所建的墨妙亭,修葺了宋代湖州太守李公择所建的六客堂,新建了纪念明代诗人孙一元的太白亭,最值得一说的,是增建原来湖州城南岘山的三贤祠为九贤祠。
原三贤祠主要纪念主政过湖州的颜真卿、苏东坡、王十朋三人,年久失修,颓败不堪,吴绮访古见到时已沦为过路人烧水煮饭之地。他于是召集工匠,重新修建,并集思广益,增三贤为九贤,将史上担任过湖州郡守且有功于百姓的东晋王羲之、谢安,南朝萧梁的柳恽,唐代杜牧,宋代孙觉以及明代陈幼学列入其中。来到这里,遥想古人,会有“脱屣富贵、摆落尘氛”的念头,更会有敬重文化崇仰先贤的想法。吴绮修建古迹,或有个人喜好的原因,但更多的目的在于教化百姓,同时代大诗人及其好友吴伟业受邀撰文,一语道明其“弘长风流、训示励俗”的作用
除了“三风太守”的名声,其实吴绮还有两个雅号。一是“红豆词人”,他幼时颖悟过人,六岁赋诗《山中吟》:“山溪清浅山花红,抗首高歌和晓风,世事回头君莫看,不如沉醉此山中”,一鸣惊人,长大后游学、苦读不断,在湖州作了一阕《醉花间》,有“把酒嘱东风,种出双红豆”之语,写出了闺中女子对爱情的憧憬,相传毗陵(今江苏武进一带)一位女子,见而悦之,将这两句写满家中四壁,日夕讽咏,“红豆词人”因此得名。但后来词家陈廷焯以为,“此类皆一时情艳语,绝无关于词之本原,而当时转以此得名,何其浅也。”这是就词而论,推而言之,此名声雅则雅矣,却传而不广,多因与百姓冷暖、社会痛痒毫不相关。
再就是“听翁”。吴绮晚年回扬州安家后,终日以诗酒自适,对上天之馈赠,贫困自得,“以修短衰健听之天,以利钝荣辱听之人,以是非毁誉听之千百世,而后流行坎止,吾何心焉!”年老渐衰后,视力不佳,以听为主,最喜欢听晚辈读诗文、他人谈野史、髫童弹丝竹,他因此自号“听翁”。这样的称号,颇有些历经繁华后的平淡自况,宠辱不惊,顺其自然,仔细体味,却有些壮志难酬之叹,因而也更多限于圈内知晓。
而“三风太守”则不同,留下的是无尽的想象。被罢官数年后,其友人王嗣槐再过湖州,与百姓闲谈,问新任太守较前任太守如何?百姓说,眼下州县吏胥上下其手,贿赂盛行,政风大坏,远不如前。对吴绮在湖州的三年,百姓的评价只一句,“求如公者而不可得”,朴实的背后是深深的想念和无比的惋惜。百姓的纪念远比他在任的时间长得多。
名声,流得进心里,才长留得人间。
